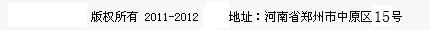梁寒,张李.早期胃癌治疗方式合理选择:争议与共识[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39(5):-.
早期胃癌治疗方式合理选择:争议与共识
梁寒,张李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39(5):-
摘要早期胃癌有其独特的行为特点,治疗的诸多方面都存在争议与共识。既往早期胃癌治疗以传统追求肿瘤根治的开腹标准胃切除和淋巴结清扫手术为主。近年来,随着我国早期胃癌检出率的提高以及外科手术器材的进步,针对早期胃癌所实施的外科治疗逐步转变为以内镜及腹腔镜机器人为代表的微创手术,以及在肿瘤根治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留胃的正常解剖和生理功能以改善治疗后病人生活质量的功能保留性胃切除术。早期胃癌的治疗模式呈现多学科化、精准化特点,对符合适应证的早期胃癌病人,内镜治疗是首选,其微创优势更加明显。对于非内镜治疗适应证的病人,内镜与腹腔镜的双镜联合手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项目(No.YFC);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计划项目(No.YFC);天津市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No.15JCYBJC);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No.KJ)
作者单位:医院胃部肿瘤科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通信作者:梁寒,E-mail:tjlianghan
. 本文将就相关争议与共识进行评述。1EGC的定义及现状胃癌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据国家癌症中心报告,2年我国新发胃癌67.91万例,死亡49.80万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居恶性肿瘤的第2位[1]。EGC被定义为不论有无淋巴结转移,癌组织仅限于黏膜或黏膜下层[2]。年全国胃癌协作组提出的EGC大体分型方法明确了普通型EGC和特殊类型EGC的分型标准,该分型可提示EGC的不同浸润生长能力和扩散趋势。需要强调的是,EGC定义本身与TNM分期系统中的Ⅰ期胃癌不尽相同,EGC仅限定为T1a及T1b病人,对N分期未做硬性要求。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基数大,我国EGC筛查工作开展得并不理想,但是近年临床EGC的检出率增加的趋势也较为明显,中国胃肠肿瘤外科联盟—年的数据[3]显示,我国外科诊治胃癌人群中EGC的检出率已接近20%,EGC所占比例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整体而言,存在南方高于北方、东北和华东地区高于华南和华中地区以及一线城市高于非一线城市的特点,而这一地域差异考虑可能主要与公共教育及人群健康意识的差异相关。在EGC的治疗方面,内镜治疗例,腹腔镜手术例,开腹手术例。在手术切除的病人中,病理学分期为T1a期的病人共例,出现淋巴结转移例,病理学分期为T1b期共例,出现淋巴结转移例。
对于EGC,常规的胃切除术和淋巴结清扫几乎能达到完全治愈的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内镜技术的的迅速发展,内镜治疗也被认为是部分EGC的治疗方法。内镜治疗、腹腔镜手术及开腹手术3类方式,给病人带来的创伤程度依次递增。因此,对于符合内镜治疗适应证的EGC病人,首选内镜治疗;对于不适合内镜治疗的病人可行开腹手术或腹腔镜及机器人手术。
2EGC的内镜治疗EGC内镜下切除手术主要包括内镜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mucosalresetion,EMR)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submucosaldissection,ESD)。原则上内镜治疗适用于淋巴结转移可能性极低的肿瘤。日本较早实施了基于其国内40岁以上人群的胃癌常规筛查,由于EGC的检出率高,故诊断和治疗多由内镜医生完成[4]。
在年2月召开的“第91届日本胃癌学会年会”上,来自静冈肿瘤中心的Ono教授做了有关EGC内镜切除现状及未来展望的报告。根据日本国家癌症登记中心数据,年日本共治疗胃癌例,其中内镜治疗例(EMR例,ESD例),开腹+腹腔镜手术例。一项包括例EGC病例(枚病灶)的多中心回顾性真实世界报告结果显示:99.4%的EGC病例采取了ESD;99.2%的病例采取了整块(Enbloc)切除;R0切除率91.6%[5]。年,Sasako[6]报道了日本国立癌中心—年内镜治疗的例EGC的治疗结果:黏膜内癌5年总存活率94.3%;黏膜下癌89.7%;而两者的疾病特异性5年存活率分别为99.3%和96.7%。
年出版的第4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7]将EGC内镜治疗的标准适应证规定为:直径<2cm、不伴随溃疡、分化型、局限于黏膜层(T1a)。扩大适应证包括:(1)直径>2cm、不伴随溃疡、分化型、局限于黏膜层(T1a)。(2)直径<3cm、伴随溃疡、分化型、局限于黏膜层(T1a)。(3)直径<2cm、不伴随溃疡、未分化型、局限于黏膜层(T1a)。JCOG研究[8]回顾性分析例符合扩大适应证(1)、(2)的采取内镜治疗的EGC病例,结果显示病人的5年总存活率和无复存活率存分别是97.0%和96.9%。基于上述结果,第5版《胃癌治疗指南》[9]将第4版的扩大适应证(1)、(2)调整为标准适应证。仍保留(3)为扩大适应证。JCOG/研究[10]同样采取了非随机回顾性研究收集来自日本51家医疗机构,符合扩大适应证(3)的例行内镜手术的病例,其最终随访结果将在年即将召开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SocietyofClinicalOncology,ASCO)年会上公布。预计在第6版《胃癌治疗指南》会将第4版扩大适应证(1)、(2)、(3)调整为标准适应证。日本目前正在启动一项有关80岁以上老年人不伴溃疡、直径≤
3cm、cT1a,b(分化型,弥漫型)EGC的ESD疗效评估研究。日本学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所有EGC均可以由内镜医生完成治疗。
对于特殊部位[如食管胃结合部(esophagogastricjunction,EGJ)]的EGC,日本的内镜医生也做了诸多工作。来自Saku医院的Oyama[11]在“第91届日本胃癌学会年会”上介绍了其中心—2年采用ESD治疗例早期贲门癌(齿状线以上1cm及齿状线以下2cm)的经验。T1b又分成T1bM1(≤μm)和T1bSM2(>μm)两个亚型。肿瘤平均直径18(2~61)mm;标本平均直径40(22~82)mm;整块切除率%,R0切除率99%,无局部复发。
EGJ早期癌ESD操作的主要难点是空间狭窄,操作困难。发生于胃部的T1bSM1癌浸润深度μm以内;而食管癌T1bSM1则定义为浸润深度在μm以内。Oda等[12]收集来自日本14医院—年收治的T1a和T1b食管腺癌病例共例,手术切除标本例,内镜切除标本例。浸润深度在黏膜下层(SM)<μm病例淋巴结转移率为20%;浸润深度在SM~μm病例中,淋巴结转移率是38%,而浸润深度在SM>μm病例淋巴结转移率高达70%。多因素分析显示,病灶直径30mm、分化程度以及淋巴管、血管侵犯是影响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因此,只要严格掌握适应证,EGJ早期腺癌采取ESD治疗安全可靠,手术器械选择至关重要,EGJ早期腺癌T1bSM1应该定义为侵犯深度<μm。
目前我国EGC内镜下切除已经取得共识的适应证[13]为:(1)绝对适应证:①未合并溃疡的分化型黏膜内癌(cT1a)。②病灶直径≤3cm、有溃疡的分化型黏膜内癌(cT1a)。③胃黏膜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igh-gradegastricintraepithelialneoplasia,HGIN)。(2)扩大适应证:病灶直径≤2cm、无溃疡的未分化型黏膜内癌(cT1a)。该共识具备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在符合适应证前提下,内镜治疗EGC已被广泛认可,在安全性和预后方面均可以接受且较手术治疗更加微创。因此,对于符合内镜治疗指征与条件的病人应首选内镜治疗。周平红等[14]回顾性分析6年6月至年12月经ESD治疗的例EGC及癌前病变病人(其中EGC例),全部病人一次性整块切除率为%,一次性完整切除率为99.0%,组织学完整治愈率为99.0%。术后出血和穿孔的发生率分别为1.74%和0.76%。术后复发率为0.04%,3年存活率为99.8%。该研究认为ESD治疗EGC及癌前病变的疗效与外科手术相似,且更具有手术时间短、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等优势。
与此同时,在我国ESD治疗EGC也同样存在争议。首先是EGC的术前T分期诊断问题。EGC的诊断主要依据超声内镜和腹部CT检查。超声内镜对病变的浸润深度、区域淋巴转移有较大的意义。但超声内镜在进一步鉴别T1a和T1b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其对浸润深度的诊断准确度同病变(隆起或凹陷)、性质(分化型与未分化型)以及术者操作水平等有关。尽管超声内镜对于EGC的诊断非常重要,同样来自中国胃肠肿瘤外科联盟的数据[3]显示,我国仅有26.0%的单位常规采用超声内镜予以术前分期。所以提高EGC诊断的准确率是当务之急。
其次,EGC病人虽然是胃癌人群中预后最佳者,5年存活率达90%以上[15]。但也同时反映出EGC中仍有一部分病人尚难获得治愈,其中淋巴结转移无疑是主要的高危因素,一些研究认为内镜下切除可能导致淋巴结转移的发现延迟,并导致包括手术和化疗在内的适当治疗的延迟[16-17]。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淋巴结清扫,则无法保证肿瘤的根治性。因此,为研究淋巴结清扫的合理性,一些研究机构使用前哨淋巴结导航技术来判断淋巴结转移的程度和范围,以此来决定淋巴结清扫的必要性及清扫范围[18]。
另外,内镜下切除后切缘阳性的问题及补救措施也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切缘阳性,并且存在较高淋巴结转移风险的病人,指南推荐行手术切除。但是在临床工作中,经常出现补救手术后病理学检查“未见肿瘤细胞,未见淋巴结转移”的情况发生,这涉及到术前需要向病人及家属交代手术并发症风险、生活质量下降以及肿瘤根治性等诸多问题。因此,对于ESD术后的补救手术应本着医患双方共同决策的原则并持谨慎态度。
3EGC的手术治疗尽管内镜治疗是EGC治疗的大势所趋。但因为术前准确的临床分期存在困难,且其操作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仅适宜在经验丰富的中心开展以确保疗效,又因为我国EGC的检出率与日韩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故EGC在我国的治疗模式仍然以外科手术为主,从中国胃肠肿瘤外科联盟的数据[3]可以看出,—年接受内镜治疗的EGC病人比例一直在20%左右,且无明显递增趋势。
由于EGC的手术治疗方式不同于进展期胃癌,故在原发灶切除及淋巴结清扫范围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对于早期胃窦部癌保留幽门及迷走神经功能、EGJ早期癌行近端胃切除而非以往的全胃切除也已经取得共识。随着微创技术的进步和腹腔镜显示设备的发展以及达芬奇机器人的出现,目前几乎所有的保留功能手术都可以在腹腔镜辅助或是全腹腔镜下完成,这一点业已被认可。
功能保留性胃切除术(functionpreservinggastrectomy,FPG)是指在确保手术根治和系统淋巴结清扫的前提下,减少胃的切除范围,保留幽门和迷走神经功能,以达到改善术后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的手术方式。对于保留幽门胃切除术(pyloruspreservinggastrectomy,PPG),目前国内基本认同了保证安全切缘和D1+淋巴结清扫策略。Hiki等[19]报道例cT1N0M0的胃中部癌病人接受PPG术后长期随访(平均随访61个月)的结果显示,病人5年总存活率高达98%,肿瘤相关病死率和复发率均为0。回顾性研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果表明FPG在肿瘤学安全性方面是可靠的,也能获得满意的长期生存。对于胃窦保留长度的争议,目前大多数学者建议在确认切缘阴性的情况下保留
3cm以上即可[20]。
目前争议较大的地方在于EGC近端胃切除后的消化道重建方式,部分接受近端胃切除术的病例术后存在胸骨后灼痛、胃饱胀及食管反流等不适而使生活质量降低。为预防这些消化道功能障碍并便于随访观察残胃,常选择的消化道重建方法有食管胃吻合、双通道重建和间置空肠等方法。食管胃吻合是最简便易行的吻合方法,但常有严重的食管反流和吻合口狭窄发生。间置空肠可缓解食管反流,但仍有较高的胃排空延迟发生率。双通道重建的操作过于复杂,但在保留功能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食物储存功能方面[21-23]。Kamikawa双浆肌层瓣成型术是日本学者Kamikawa于1年首先报道并应用于EGC近端胃切除术后食管-残胃重建的方法[24]。目前该方法仅限于日本学者的零散病例报道[25-26],笔者所在中心亦曾尝试过此术式,操作稍复杂,对精细度要求高,短期抗反流效果可靠,但还需要临床研究以证实其长期优势。
随着内镜成像系统及手术设备器材的不断进步更新,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更加精准的双镜联合手术是EGC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特别是对于考虑有淋巴结转移的EGC病人。双镜联合手术术中先通过胃镜进行肿瘤定位,同时建立气腹,行腹腔镜监视下的EMR或ESD,如果内镜治疗后出现胃壁菲薄、穿孔或出血等,可于腹腔镜下行胃壁修补或缝扎止血处理。如果肿瘤在内镜下处理无法达到根治的目的或切缘阳性,则由外科医生在腹腔镜下行EGC的胃腔内黏膜切除术、胃楔形切除术或胃癌根治术。对于直径<2cm,分化良好但有潜在淋巴结转移的病例,也可施行ESD+腹腔镜淋巴结清扫。在内镜下于肿瘤周边注射示踪剂,腹腔镜下取前哨淋巴结行活检,以确定淋巴结是否有转移。Tonouchi等[27]为6例EGC病人行EMR后腹腔镜前哨淋巴结显影,行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根治性手术,6例病人共检出20枚前哨淋巴结,85枚非前哨淋巴结,术后病人均无复发。双镜联合手术既保证了合理的淋巴结清扫,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胃的功能,充分体现了精准手术的治疗理念。当然,这也对内镜医生和外科医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综上所述,EGC的治疗模式呈现多学科化、精准化特点,内镜与腹腔镜结合可能是未来研究的热点。同时争议与共识并存,为临床诊疗带来更多契机和更高要求。临床医生应根据医患双方的实际条件,以“最适合”原则,保证肿瘤的根治性和良好的预后效果,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减少创伤,提高术后生活质量,为病人带来更大福音。
(参考文献略)
(-04-02收稿)
版权声明
本文为《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原创文章。其他媒体、网站、